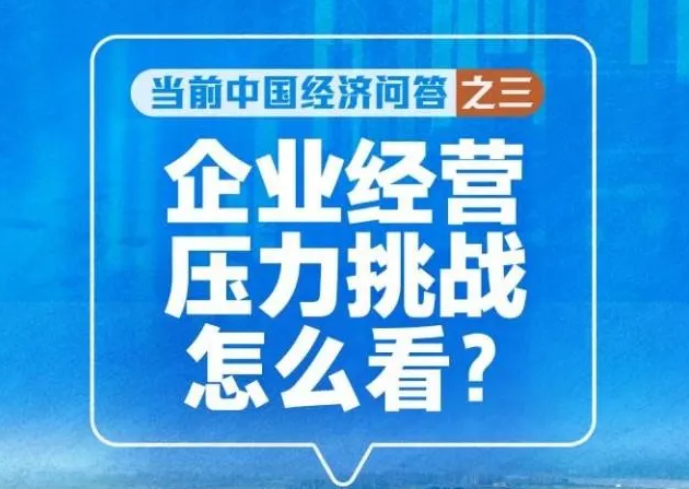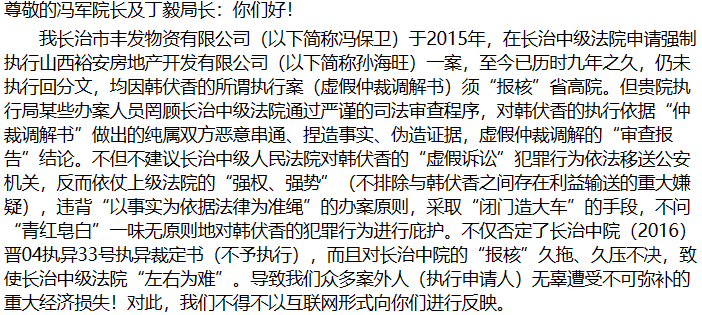从“权威人士”访谈纪录一窥中央政府高层的经济观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撰文指出,本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局首季问大势》共有万余字的访谈纪录,最受注意的似乎是“权威人士”说中国经济的前景是L型,不是U型或V型。但访谈中更重要的价值是我们从中可一窥中央政府高层的经济观,并可据此推测将来的经济政策。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惊一乍 有欠稳定
若“权威人士”真的能代表中央政府的看法(此假设未必正确,任何政府对经济政策都会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那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正在中国扎根。此学派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在美国以芝加哥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为主要根据地,两校都因此出过多位宏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用今天内地流行的经济界术语去描述,此学派非常重视“供给侧”政策,即认为结构性改革、制度、教育科技等等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因素,远比凯恩斯式的以刺激短线需求为目标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来得重要。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另一特征便是强调“预期”的重要性。一个政策若早已为人民预料到,便会失去有效性。例如,央行若事先张扬,预告下周会把货币贬值,那么市场必会立即行动沽出该货币,贬值便会立时出现,不会等到下周。因此,不少宏观经济政策若要产生政府所希望达致的效果,便必须是突如其来,少人预先想得到的。
不过,有效果的政策却并不一定可取,此种无法预期,一惊一咋的政策会变成市场新的震荡来源,长远而言,对经济的稳定性并无好处。“权威人士”表明“稳预期的关键是稳政策”,他反对以“半夜鸡鸣”形式出现的政策,在学理上等于他认同新古典学派,经济政策不应因追求短线的效果而长远地造成更大的波动,故政策要透明可预期。我相信对大部分政策而言,是否可取比是否有效果更加重要,但经济政策上也确有不少例子,是要突如其来执行的,否则反而误事,上述贬值(或升值)的做法便是一例子。
“权威人士”认为当今中国要解决的部分问题是去产能、去库存。但怎样“去”呢?中国某些行业显然出现了产能过剩或产品过多卖不出去,煤炭、钢铁甚至是某些城市的房屋都是例子,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也有大量行业产能不足,例如环保行业、不少高科技或医疗行业,其产品都需求正殷。
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无论扩张性还是收缩性的,一般都并非标靶性的,它们会同时影响所有行业,不会在压缩产能过剩行业的同一时间又使到产能不足的行业得到扩张。本来产能过剩出现的主因是这些行业并未受到自由市场力量的约束,否则若产品卖不出去怎么还不自动减价及减产?但在中国,这却涉及解决一系列结构上的问题,例如长期亏本的殭尸企业救还是不救?
下岗的工人若要转行,在过渡期间其生产力必然下降,他们过去掌握的技能会失去大部分价值,学习新的技能也需时间,所以转型的规模若大,生产力下行的压力便愈大,中国正在多条战线上要转型:农村人口转到城市,劳动密集工业转为高科技产业,制造业转为服务业等等,这些转型,L型的经济走势的确不易很快结束。
创新力量 挑战硅谷
在“权威人士”提出的问题中,“高杠杆”较为复杂。所谓“高杠杆”,我的解读是指“欠债股权比”(debt-to-equity ratio)高企,可能会对经济带来风险。有关债股比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奠基之作应是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莫迪里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这里可简称“莫米定理”)。“莫米定理”的一个版本十分简单:在一定的条件下,一所企业的债股比对该企业的价值并无影响。
此定理的直观解读倒也容易,我们可用投资房屋说明问题:假设一所房子值1000万元,但我们可以有多种方法融资买这房子,一种方法是向银行借700万元,自己出钱300万元;另一种方法是向银行借900万元,自己出100万元,无论我们用哪种方法,债股比是7比3还是9比1,房子的价值都不会有变,仍是1000万元。房子的价值受其质量及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与资金从何而来没有关系。同理,企业的价值亦与其债股比无关。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接近GDP的50%,等于美国储蓄比率的三倍,其中等于GDP 46%左右的储蓄会通过银行借贷、企业债券及股票等等途径投资到企业或地产中。又因中国股票及金融市场并不发达,只有不足一成的新增资金通过股票投资,其余的主要是靠人民把钱存放银行,后者再把资金借给企业,也有直接买入企业发行的债券,但数量不大。既然如此,中国的债股比必然高企,通过直接或间接方法借钱给企业,依然是每年新储起来的资金投放到企业的主要方法。债股比高企,是中国人民储蓄率高,社会中资金充裕的后果,不能简单视之为坏事。
高杠杆或高债股比会否带来风险?这当然有可能,港人经历过2003年的负资产潮,对此应深有体会。假设一所楼宇或一所企业的债股比是7比3,但因市场或经济因素,楼宇或企业的价值下跌超过三成,那么负资产或银行的坏账都可能出现。通过向企业贷款,债权人的目的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回报(利息),不愿承担企业本身的投资风险。
企业的股权拥有人则是希望通过高杠杆,用较低的利率借到钱,从而扩大自己投入的资金的回报率,代价是自己要承担所有风险。但一旦出现负资产,亦即企业面对的下行风险太大,此种模式便乱了套,企业可以选择破产,后果可能比负资产更划算。企业剩余的资产会成为银主盘,价值进一步剧跌,银行所发放的信贷变成呆坏账。换言之,股权人有可能把本应自己承受的商业风险转嫁予不应承受风险的债权人,并引起连锁反应。高杠杆因此可以把企业的商业风险扩大为社会中的金融风险。
上文提过,“莫米定理”需要一定的前设条件才能成立,其中一个条件与税制有关。一般而言,公司因借入资金而要付出的利息,会视之为公司的成本,因而可以少交一点税,但融资方法若是靠卖出股权,那么股息在内地及不少国家都是要交税的。由于征税的不对称性,企业融资时应尽可能通过借债,从而达到避税及提高到公司价值的目的,总之是债股比愈高愈好,股权人不用怎么理会此举可能带来影响金融体制的风险。
政府若要应付,可能要作出监管,限制债股比,但若由市场本身去处理这问题,银行或债权人则大可一早把上述的风险都考虑在内,提高借贷利率以作风险的补偿是也。近日内地时有债转股的建议,其目的也是在欠债的企业一旦出现较大的压力时,可及早把风险和部分股权较为有序地转到债权人手中,它不能减低企业的投资风险,但可减低负资产企业破产的可能,从而减少金融系统的风险。在股票市场并未发达,债务为主要融资手段的历史条件下,债转股虽并非没有代价,但也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手段。
“权威人士”的访谈另有一段说话颇为有趣,让人可窥见其经济产业的发展观。众所周知,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完美,但现在中国强调要搞创新,这会否与知识产权的保护相矛盾?若有人想出新意念后,一经推出,立时便被人抄袭,创新所能带来的红利便可能快速消散,谁还会愿意创新?抄袭别人岂不更好?
不过,据一些熟悉中国创新科技的国际评论家所观察,说中国只懂抄袭(而中国的确善于抄袭)已是极为过时的观点,北京深圳等地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加州的硅谷形成挑战。一个例子是腾讯的WeChat,连Facebook也要反过来抄袭它。既然知识产权保护不周,为何中国仍可有创新的力量?我认为关键应该在于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消费者人数等闲以亿计算,就算创新意念会遭人抄袭,当中过程也需要时间,但因潜在的消费者太多,在抄袭者能构成竞争压力之前,创新者已可赚取庞大利润,这便足够提供动力,使他们肯努力创新。
暴力救市 背有民粹
“权威人士”似乎也很清楚在有人成功创新或打出一个新的市场或行业后,会有很多后来者接踵而来,加入战团,在市场中要分一杯羹,“权威人士”称此为“产业同构化”,意即大家都做同一件产品,这自然会拉低利润,最终大家都再无利可图。“权威人士”并不介意出现此种饱和情况,因这会带来第二个阶段,即他称之为“分化”的阶段。既然在同构化的行业中大家都无钱可赚,那么自然有企业会离开,另外创造一种新产品,进入一个新市场,他们便又再在新的市场中重复第一阶段,生生不息,产品也就多元化。“权威人士”这个论述,在经济学上算不上新鲜,但在市场规模庞大又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似乎也说得过去,也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创新产业近年变得如此有活力,一所所世界级的企业陆续涌现。
为什么“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可不断进行结构性的经济改革,而不用乞灵于短线的刺激需求?他认为西方国家有多党执政的痼疾,没多少政治家敢于面对结构性改革带来的阵痛,所以他们只能治标不治本,改用财政及货币政策去催谷经济,最后造成金融海啸及欧债危机此等大祸。中国的领导人的确不用考虑选票,但这是否意味他们便可不理民间和利益集团的压力?
我看这只是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去年中央的“暴力救市”背后怎会没有民粹的压力?一旦股市跌得惨重,随时也可能有人要承担责任,甚至落台。我们也不能期望中央政府可以完全不理改革的阵痛,不采用任何短线的刺激政策。(文章来源:hkej)
(责任编辑:李士英 HN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