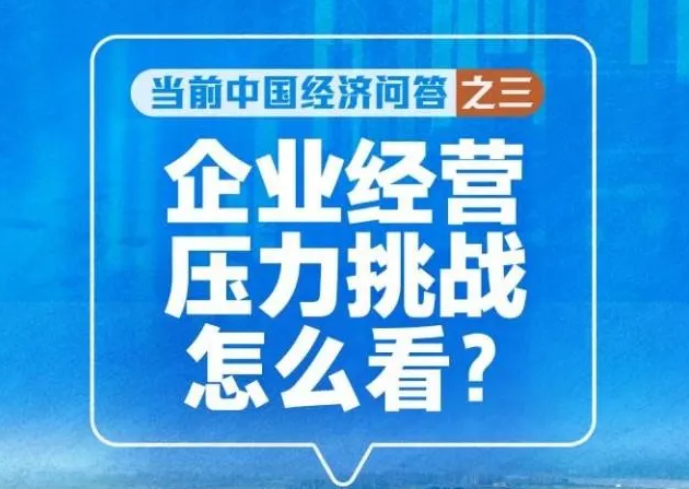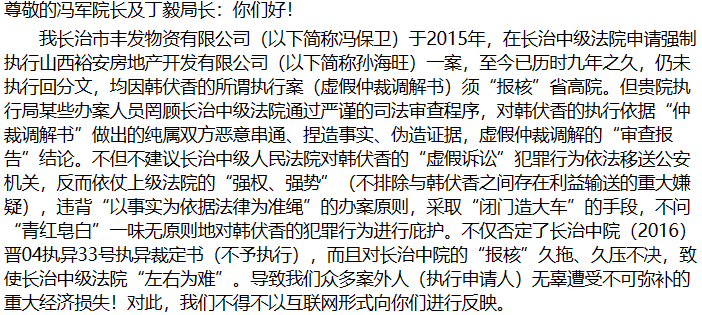徐惠泉墨彩人物画上的斑斓
金投收藏网讯,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具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特点。
南唐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仔细去看这幅体现中国古代人物画最高成就的长卷,画面中,有些地方并没有清晰画出墙壁、门窗、屋顶,也没有烛台、灯盏之类来显示光影和明暗关系。人物在充满空白的场景中悉听琵琶,击鼓观舞,更衣暂歇,直至曲终人散……犹如中国古典戏剧,一桌一椅一屏风,就是整个客观存在的寓言。于物质世界,做的是减法,人物造型的浮雕感也是平面化的――那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观察方法――最写实的地方也给人一种虚幻感。仍然像中国的传统戏剧,当男性角色提起戏装的前半幅衣服,这个简单的动作却可以随意引伸为三层意义:行路前心情急切的准备;无可奈何,心烦意乱;以及与相关人物地位的差别:即将下跪。
这些图卷中,人物用手势或者眼神夸张地活动,或者干脆静止,却总是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在想着什么,等待着什么,而且在这种冥想和等待中,时间和空间对他们不造成丝毫的困扰。
中国的山水画中也有人物,即使他们表现出细微的情绪哀乐,但总的来说,他们并不朝向看客与观众,而是面对永恒的道极。他们也在想着什么,等待着什么,但人物面部永远不会出现冲突或者挣扎的表情,他们总是淡然而适宜的,至多只是探身看一看这个幽深莫测的世界。
在东方背景和古典传统中,人的能动性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强调的。所以在一个最根本的意义上,力量来自留白之处,来自画面之外,一切都同恒河水顺流而下,一切又具有某种神秘性――即使是在工细灵动、设色雅致的工笔人物画中,这种无法言说的神秘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以上这些,也正是我要叙述的画家徐惠泉,之所以在人物画创作中取得杰出成就、同时又面临诸多困惑与挑战的基点所在。
有一次聊天,徐惠泉和我谈起并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在中国绘画中,人物画是最有可能向前推动的。
观点的源头或许起源于徐悲鸿。当年徐悲鸿留法归国后,曾公开撰文对中国画做出评价。他认为中国画最好的是花鸟画,其次为山水画,人物画最差。中国画的两大致命伤在于:第一造型不准;第二,明清以后临摹至上,使中国画与现实的联系变得愈发僵化寡淡。所以,徐悲鸿当年竭力推崇引进西画的写实方法和素描写生的造型训练,并称之为对于国画的“写实改造”。
然而,这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悲壮实验,至少从艺术上来说。因为中国画具有极为特殊的精神内涵。在本质上,中国画是一首诗。不管是用什么笔墨方式来表达的,好的中国画必须能归结为一首诗。虚实相生,阴阳之道,里面终究要有混沌的东西。而徐悲鸿进行的其实是一次技术层面上的改造,就像把那些虚化的墙壁、门窗、屋顶一个个安装上去,房子完整了,味道却全然没有了。
实验固然失败,但观点的源头却不无道理。或许,徐惠泉对于人物画可能性空间的信念也正在于此――怎样在“形”与“意”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既把形象画准,又不能太油画化,还要在根本上保留东方精神的神秘性?
在探索的过程中,徐惠泉做了一件非常重要、也是根本性的事情。不论是潜在的艺术直觉,还是可贵的有意尝试,在徐惠泉的艺术构成中,自始至终没有丢弃笔墨的表现性。水墨的用笔和气象,是他人物画中有意无意的一个“无底之底”。那些斑斓的色彩,是墨色之上的枝叶和涟漪。水墨是东方之境,色彩则是现实在虚境中的倒影。很长时间以来,徐惠泉的人物画被定义为彩墨人物画,这或许是一个误会。不如称之为墨彩人物画更加合适吧。
在人物画中,对于造型和线条截然不同的处理,是东西方绘画的重要区别所在。
中国画讲究线条,虚虚的一根线,命若琴弦,里面藏着乾坤万千。造型则是建立在线条基础上的。中国画重视笔墨,同时更讲究“笔性”,讲究线条的质量、美感,讲究线、形的透里默契,刃剖自如。
中国古人画肖像的时候,脸也有立体感,但不画体面,剔除光影,只画“结构”,这被称之为“洗脸”。在这个基础上,进而要求生动性,学会夸张和变形。
而在西方绘画中,空间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许,根本意义上对于“力”的理解构成了这种区别。中国画消解人为的力,因为归根到底,天人终究要合一;而西方绘画强调人为的力,雕塑家罗丹甚至高喊:“牢记罢,只有体积,没有线条!”就像去看一张拉斐尔画的肖像,画正面的人时,他把胸部曲折地推远了,于是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第三元空间。
对于一个把人物画作为自己创作目标,并且力求突破的画家,在人物造型和线条处理方面,徐惠泉显然具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重视线的构成,如果说徐惠泉已经用笔墨铺陈出一个“无底之底”,那么,他笔下极具张力的线条则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线是纯粹的,也是繁复的;看起来很简单,细看则又是令人迷惘的;有序里显现无序,无序中又能找到万物归一的逻辑。他笔下的画面总体是平的,但在有些画里,人物脸部的留白又在提示另一种可能:光影其实是存在的。
徐惠泉是一位勤于思索的画家,这同样在他的色彩运用上体现了出来。他用重彩,但显然他不想成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工笔重彩画家,就像他始终没有轻视笔墨一样,他让笔下的色彩染上了一种奇妙的写意感。重彩竟然也能是微妙的,它们并不完全落到实处。不仅如此,光影的感觉在色彩中再次被强调。这种不落实的墨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巧妙地到达另一种虚境。而只有在虚境里,才能真正呈现中国画本质的意义。徐惠泉做到了。
然而,在线条、造型以及色彩之后,另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因为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件艺术品,是单靠着线条的均衡、美丽的色彩而能打动人心的。如果,十二三世纪时,那些花玻璃深蓝天鹅绒的感觉,柔和的紫光和热烈的绯红能感动我们,其实是因为这些色调是传达当时人们对于天国的想望与神秘的默想之故。如果宝蓝色的波斯古瓶是可爱的珍品,那是因为它们多变的颜色,把我们催眠,引我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神仙境界中去之故。
一切的美都应该是有意义的。
于是要论到题材。
徐惠泉说过这样的话:“我画既熟悉有又点陌生的人物,她们有窈窕的的身材,姣好的容貌,但她们命运多舛,因此姣好的容貌总带着丝丝的忧愁,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幽香,远处有隐隐的钟声传来。”
这样属于南方的语境,或许才是徐惠泉不断寻找新的艺术语言,来进行崭新表达的底色所在吧。
徐惠泉梳理过一次中国人物画发展的脉络与走向。在时间概念上,寺观和石窟壁画可以看作中国人物画在宗教艺术的高峰,远甚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绘画的艺术水准;中国人物画的真正衰落是在北宋以后,以王维、苏东坡开创的文人画崛起,进入了以山水花鸟为主的中国画另一阶段。其中,色彩观也转向文人趣味,将水墨作为主色,将“淡雅”视为一种文人趣味,而将山水花鸟画中的青绿等鲜艳色调视为匠气的“趣味”。人物画前进的步伐几乎完全停滞,而此时的西方,人物绘画则一步步清晰地解决了人物肌理、光和色彩、直至立体主义。
我知道徐惠泉最终的理想在于“打通”。但难处仍然在于“打通。”而是否能够“打通”则是评价一个画家段位的重要指标。就像人们对于徐悲鸿的评价“刚刚及格”,他的短处之一,就在于他对于西方现代美术表现形式的排斥。刘海粟至少还接受了印象派,但走得最远的是林风眠,林对于艺术的探索已经扩展到毕加索、马蒂斯等人,他一直尝试在做的,是在中国绘画传统中寻找现代主义的形式资源,并将其改造成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画无中西之分,只有好坏之别”,这几乎是一个最高的艺术理想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有些细部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伪命题。就像徐惠泉对于中国人物画走向的深入思考,把它的意义外延进一步进行拓展,其实质,已经是一个如何在中国绘画的本体内部重新激发创造力的象征性议题了。徐惠泉的墨彩人物画,以及它走向的可能性,于此基础上,充满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