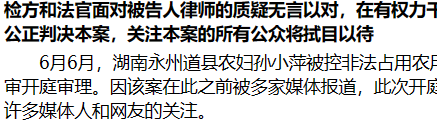暗香浮动的古诗风韵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声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慵懒的春天,暖风拂面,女主人公玉纹提着篮子行走在城墙高处,画面中,残破的墙砖堆满视线。与此同时,昔日恋人同时也是现在丈夫戴礼言的好朋友章志忱,正伴着暖暖阳光从上海赶向礼言家大院。作为医生的章志忱此行目的一来是好友相聚,二来是为礼言治病。在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娶了自己的初恋情人。电影的背景设置在抗战结束后的一个春天,万物复苏,人们也自然而然要联络一下久违的感情。而住在小城里的礼言和玉纹夫妻却终日死气沉沉,仿佛春天还没有降临那里一样。
由于礼言身体孱弱,就像这个受尽摧残的大地,一直都没有人修复,以至于毫无生气。本来活泼的玉纹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也渐渐冷却了一颗炽热的心。而志忱的到来,如同一股暖和的春风,熏陶出清新的气氛;又如同一粒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泛起阵阵涟漪。礼言开始活跃了,玉纹更是被这道久别重逢的暖风吹得渐渐复苏了,佣人老黄甚至推开了书房关闭很久的九扇大门,让阳光洒满这个尘封多年的旧宅。志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活力,给死寂的家庭带来希望,与其说他是个闯入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旧制度”的改换者,促新者。他令玉纹回到了从前而有了展望未来的想法,他让好友礼言多添几分生活的信心,重燃坚强的勇气。
影片结尾,礼言被病情折磨得服药自杀未成,志忱离开小城。礼言对玉纹说:“待我把病养好,我们重新过一种有希望的生活。” 镜头最后,玉纹坐着绣花的姿态楚楚动人,风情的旗袍绰约着她一张温和的脸,细细的阳光透过窗棂谅解地呵护着她,婉转的音乐潺潺流畅……
虽然影片平淡如水,但是人物之间的诚实善良和真挚情感弥足珍贵,如庭院中的花,氤氲而芬芳。电影的语言、画面、隐喻处处体现出中国传统诗词的幽雅意境,这也是笔者在开篇引用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的原因,影片的氛围和唐诗宋词可谓是做到了相当完美的和谐统一。难怪有专业影评人这样评价说:不能忽视费穆先生作为一位永恒的不朽的传统的创新的电影大师在把现代电影的记录本性和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完美融合中所作的努力。《小城之春》的先锋,就是那种中国古诗词时空交的错感和意境,这才是《小城之春》最伟大的地方。
当然,《小城之春》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意义:它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心理写实主义的先河。影片直面传统伦理和个性张扬的矛盾和冲突,对这种敏感的话题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充满了大量的人物心理活动的表现,这在之前的中国电影作品中是罕见的。导演费穆调动了很多种手法来进行心理描写,比如全片通过玉纹的个人独白贯穿始终,利用独白展现主人公两难的境地和强烈的思想挣扎,并且与画面配合得丝丝入扣,别具一格。
当然,《小城之春》这部影片不单单是讲述纯粹的男女之情,而是讲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最渺小的的人的心理,那是一种未知的东西,糅合着苦闷、惶惑,甚至颓废。然后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转入个人细小的情感涡流,导演费穆的聪明也在于此。
《小城之春》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反响。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如同梵高生前不受重视的画作一样。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举办了一个中国电影展,本来一直默默无闻的黑白电影《小城之春》才重新浮出水面并引起轰动。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艺术家们,被这部情节简单却寓意深邃的作品深深感动,评论说,费穆的这部诗化电影,与日本电影《罗生门》和美国电影《公民凯恩》一样都属于世界电影的经典杰作。2000年在一次香港影评人集体推选的十大中国佳片中,《小城之春》名列首位;在中国五大电影导演的名单上,费穆又名列第一位。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影片开始后不久,礼言望着小园里萌动的绿意说,春天了呀……是的,春天是又一次循环的开始。而春天讲述的,除了新生之外,也许只能是回归。